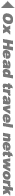城市发展的四个阶段中国城市发展研究

“人烟衰少”的荒服之地逐步发展成为“东南大藩”;从文教落后的蛮夷之区,变化为“文儒之乡”;其经济建设和对外交流(包括海外贸易和文化交往)更获得长足的进步,福州因此而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对外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繁荣门户

“人烟衰少”的荒服之地逐步发展成为“东南大藩”;从文教落后的蛮夷之区,变化为“文儒之乡”;其经济建设和对外交流(包括海外贸易和文化交往)更获得长足的进步,福州因此而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对外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繁荣门户。这是继史籍记载的、东汉时期作为王朝南方“贡献转运皆从东冶”的海上交通贸易枢纽之后,更上层次的发展,对福建社会历史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记载,“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逋迩郡邑。穹林巨涧,茂木深翳,小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墟。”闽中“在隋,犹以为一闽县耳”。当时,光是州一级建制自南朝陈永定初(557)始建闽州起,其后屡经兴废、更改。如隋初平陈之后(589)改名泉州,唐初(618)改建州,不久又改泉州,后复改闽州,直至开元十三年(725)才改定为福州。所以上引“始州”,应指陈、隋至唐前期的百余年时间。其时福州区域内地旷民稀,近城才有农人耕作,离城稍远的山丘林峦,便都是野兽出没的荒芜之地。
汉魏六朝,北方中原地带战乱频仍,民无安居;不仅州县行政,隶属无常,名门大族也随同平民百姓,迁徙。到隋唐以后,“户口既蕃,衣冠始集”。南方各地,出现许多侨置郡县。所以到隋朝短暂统一时期,对州郡县进行大量裁并。福州人口并无大增(史载晋代晋安郡人口仅4300户),在南朝陈永定初,升为闽州(郡治在闽县),领三郡(建安、晋安、南安),开始成为刺史官的治所,陈宝应任闽州刺史;天嘉六年(565),陈宝应失败,闽州废除;光大元年(567),恢复升为丰州。隋开皇九年(589),平定陈朝之后,又改名泉州,废除建安、南安二郡,全归泉州(今福州)管辖。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复改闽州;大业三年,又改建安郡,下辖闽中,只设四县(闽县、建安、南安、龙溪),治所仍在闽县。唐初武德元年(618),改建安郡为建州;四年,移建州于建安(今建瓯);六年,又从建州中析置泉州(今福州),下辖闽县、候官、长乐、连江、长溪五县。武德八年,设置泉州都督府,管领建州、丰州(南安)。到景云二年(711),又改为闽州都督府城市发展的四个阶段,管领泉、建、漳、潮共五州。直到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改名福州都督府之后,福州之名从此稳定不变,且其作为闽中首府、八闽都会的地位也从而固定。嗣后设泉山府兵、置经略使,表明大唐政权对福建的行政管辖逐步加强,并且加大了军事管理的力度,因为当时朝廷对边裔之地,需要更多的武力镇守。
唐代初期及中期,今福州地区经济未得大开发,故民生俭啬,又因文化与政教未普及,故民风朴蛮。如独孤及称:闽中“岭外峭峻,风俗剽悍。岁比饥馑,民方札瘥”。(《送王判官赴福州序》)刘长卿作诗云:“夷落人烟迥,王程鸟道通”,“君去凋残后,应怜百越空”。(《送乔判官赴福州》)皇甫冉诗曰:“辛勤万里道,萧索九秋残。月照闽中夜,天凝海上寒”。(《酬李郎中侍御秋夜登福州城楼见寄》)所咏写的闽中地尚是一片荒寒景象,北人皆视为畏途。
唐朝立国以后,考虑到福建“惟在边镇,首谨兵防”,故其建置中,先后有泉州都督府、闽州都督府、福建经略使等名称。后因“内外悉治军戎,大府要藩,始专节制”,福州作为“大府要藩”,也开始设置防御使、节度使。大历以后,朝廷“向意风俗”,故置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等,名号不一,实皆为“总统一方兵民之寄”的封疆大吏,是以统御兵戎、镇守边疆为主的钦差藩镇。其主要职能在统兵守土,于福建尤其如此。故管元惠在唐开元十九年(731)于福州城内置泉山府兵(又称折冲府兵),员额一千二百人。都督府衙之东驻兵,并辟有练兵习武之毬场。
晋安郡初创时期,首任郡守严高在筑城、修堤的同时,还开浚了东中国城市发展研究、西二湖,其后湖水灌溉福州城郊外农田。中唐以后,福建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改观。福州城市也有很大发展,不再是“户籍衰少”之地,而福建已然成为王朝的“大藩”。“州治其中,有中州气象”,说明福州作为治所地位重要,所以社会经济文化开始繁荣兴盛。唐代福州人口和社会的发展,也可以从中和年间福建观察使郑镒开始修筑州城东南隅之城墙与护城河中见到信息。到晚唐文德元年(888),陈岩主政闽中,自称观察使,也“复修”州城,所谓“恢其形势,甃之砖石”,对城池进行了扩大和改造。
王氏入闽主政,因官员大增,衙署扩大,市井繁荣,故先建罗城(大城),自冶山向南推进至今安泰河前;不数年,又修建南、北月城(俗称夹城),再次拓城至今南门兜,括三山于城中,北跨越王山。又仿长安城规制而建坊巷宅第,以安部众,为“守地养民之本”。因大规模筑城造桥,遂使州城内外“镜莹虹横,交舫走蹄,斯大城之制也”。大城滨江通海中国城市发展研究,故而“岸泊艓艛”,“悉通海?”。《三山志》云:“伪闽时,蛮舶直达福州城下”,表明海上交通便捷发达。
到了中唐,李承昭于肃宗上元二年(761)被授为福建观察使兼福州刺史,于邵为之代撰《为福建李中丞谢上表》,中称福州为“闽越都会,东南重镇”。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在《送福建观察使高宽仁序》中也指出:“福建大藩也。其地东带沧溟,南接交广,居民若是其众也,政务若是其烦也。”说明福州作为大藩首府,对外交往、贸易繁盛,因而民众政烦,自与“都会”“重镇”地位相符。
《三山志》载,虎节门外,“旧街东民居于沟外设店铺,中为廊,以便行者往来”。表明旧子城护城河外早已是商贸发达之区,店铺林立。1958年考古发现,在今东街口一带有唐代商铺和连排的炉灶,证明其时还珠门外、大航桥南边,也是商贸繁盛之地。唐末五代,安泰河两岸、利涉桥边,更是繁华竞逐的城市生活兴旺之区。据《榕城景物考》载,唐天复(901—904)初,为罗城南关,“人烟绣错,舟楫云排,两岸酒肆歌楼,箫管从柳阴榕叶中出”。生动地反映出罗城南关一带、利涉河岸边居民生活的富庶繁华。
中唐以后,不仅福州城之东、西郊外被辟为农田,而且据福州刺史裴次元诗咏,站在冶山之上往东面远眺,弥望丘原,一茶园。元和八年(813)福州观察推官冯审所撰《毬场山亭记》碑中,载述刺史裴次元为冶山二十景写了二十首诗歌,其《芳茗原》诗云:“族茂满东原,敷荣看膴膴。采撷得菁英,芬馨涤烦暑。何用访蒙山,岂劳游顾渚。”盛赞福州城东平原上茂盛生长的茶树,其品质不逊于当时剑南蒙山和湖州顾渚所产名茶。福州产茶,唐时已颇知名。《三山志》载,唐宪宗元和间(806—820),诏见福州方山(今五虎山)院僧怀恽到麟德殿说法,皇帝赐茶,怀恽即奉对称:“此茶不及方山茶佳。”《唐书·地理志》亦载:“福州贡腊面茶。”除产茶之外,从唐代闽中向王朝进贡的土产中,也可见福建的特产还有如蕉布、海蛤、文扇、橄榄等。
唐代福州人的社会生活,从《三山志》的描述中可见端倪,因为其时去唐未远,与唐代的生活状况及士民风习应当相差不大。如志书“土俗”类记载,福州地区“得天之气,和平而无戾,燠不为瘴,寒不至冱;得地之形,由建剑溪湍而下,泉莆潮涨而上,适至是而平。”这是对福州自然、地理状况与山川形胜简要而准确的描述:气候温和,寒热不至极端;地势平衍,江水海潮亦成平流。著者注意到,这样的生态环境也影响其间生民的人文性格:“其性舒缓,其思强力,可以久安无忧”城市发展的四个阶段。作者从福州自然、地理和人文方面的优势出发,由衷地发出感叹:“真乐土也”。
对于乐土上生民的治生手段与文化习俗,梁克家作出较为全面的概括:“产惧薄以勤羡,用喜啬以实华”。表明闽人治产勤谨而用度俭啬,故而常保丰足而且华实。重要的是,梁氏还生动地形容了闽中“四民”(士农工商)的从业特点:“其君子外鲁内文,而小民谨事畏法。市廛阡陌之间,女作登于男。四民皆溢中国城市发展研究,虽乐岁无狠戾;能执技以上游四方者,亦各植其身。”他描述读书人内有文彩,百姓恭敬谨慎,经商务农,女子胜男,人民各执其业,生活安宁平和。他最后概括的福州社会生活风貌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丰年治世,气象闲暇,习尚可视齐鲁”。此处“习尚”云云,应指福州经长期教化之后,开始形成如邹鲁一般的习儒重教之风。这里之所以大段引录《三山志》中关于福州社会风貌、民间习尚的记载,因为它与传说中的郭璞《迁城记》(或作《迁城铭》)所记内容可相印证:“千载不染,世代兴隆。诸邦万古,繁盛仁风”。“势气盘拏,遇兵不馑。遇荒不掠,逢灾不染”。六朝时期,北方遭受“五胡乱华”、十六国轮替之苦,百姓荡析离居;晚唐又有“安史叛乱”“藩镇割据”,而吾闽皆“无与”,保持一方晏安。
唐初抚定福建之后,闽中“丁氓日滋,庸调浸繁”,人口增长,民生富庶。福州自晋安郡治“迁城”以来,除了唐末黄巢部队毁城杀人,将福州“焮荡殆尽”,“焚殄无遗”,以及五代王审知后裔为争权夺位而互相攻杀之外,直至梁志写作的时代,长时期保持着社会安定,民生富庶,百业兴旺。正由于黄巢毁城,导致地方文献无存,而中原人士对福建又极少记载,故六朝至隋唐,闽中载籍阙略,人们只能从唐代传留至今的少量诗文碑铭中,寻觅若干残断的记录,真如吉光片羽。其时社会民生的踪迹形貌,可供追索的资料十分有限。
早期的资料中,有唐初(一说是中晚唐)包何的《送李使君赴泉州》诗,曰:“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从李使君受任为一方节镇,又是朝廷分符命将的重臣而言,他所就任的应是福建观察使(或节度使)之类要职,其驻节地也应在福州,“泉州”乃是隋代及唐初福州的旧称。诗中虽不乏夸张形容之词,但其传递的基本消息却是可信的。州城市井中多有来自海外“十洲三岛”的番商与贡使,为的是向皇帝朝觐或输贡。无独有偶,晚唐观察推官冯审于大和八年(813)所作《毬场山亭记》碑,残文亦曰:“迩时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写明海外番商客人日多一日,居留福州,长此以往,甚至影响州城内的风俗习尚,致令难保常态。更有意思的是,碑刻残文还提到州城“廛闬阗阗,货贸实繁”。描写彼时福州市井繁华、贸易兴旺的景象,正好可与包何诗句相印证。晚唐徐州刺史于乾符二年(875)作诗《送福建李大夫》,有句称:“秋来海有幽都燕,船到城添外国人。行过小藩应大笑,只知夸近不知贫”。表明福州对外交往频繁,常有外国人随船到城,而且作为大藩与富庶之邦,也令他羡慕与赞扬。
隋唐以前,福建经济尚未开发,文教也不兴盛。如唐代中叶文学家独孤及所言:“闽越旧风,机巧剽轻”,“犹有无诸、余善之余俗”。(《毗邻集》卷9)他还说:闽中“岭外峭峻,风俗剽悍”。诗人刘禹锡则称“其民悍而俗鬼”。总之,民风不离野蛮、强悍,正是文教未兴的蒙昧状态。
里人林谞在唐大中年间(847—860)所著《闽中记》中称:福州“自晋、宋文雅以来,教化丕变,家庠序而人诗书”。唐杜佑《通典》卷182也记载:“闽越”地于“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阊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可见到唐代中期以后,经过多个世代的教化,闽中士民文化程度有较大提高。说明自六朝以来,历任闽中主政官员在施治行政中,布施朝廷教化,大力倡教兴学,因而收到成效。开元十七年(729),曾任福州刺史兼福建经略军使管元惠的墓志铭中,就记有他在福州任上的治绩,称他不仅有“聿敷朝化,诱彼闽越,俗成邹鲁”的教化成就,而且提到他创置“泉山府兵”,使“海服孔淑,闽落允怀”的劳绩。该碑所记,正是福州誉称“海滨邹鲁”的滥觞。
唐代福州文教出现兴盛局面。除了管元惠的治绩外,史志多记载有中唐时期李椅、常衮“尊教劝学”之绩效,更加功不可没。唐代独孤及在为福建观察使李椅写的《李成公去思碑》中记载,李椅于大历七年(772)就任福建观察使,到任伊始,曾亲自视察州学,见“堂室湫狭,教学荒坠”,即令迁往州南地势高敞爽垲之处。继而崇学校,厉风俗,尊礼士子,“教之导之”,“乃以五经训民,考教必精,弦诵必时。于是一年人知敬学,二年学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贤不肖竟劝。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儒风济济,被于庶政矣。”一改以往“闽越旧风,机巧剽轻”,而为“比屋为儒,俊造如林。缦胡之缨,化为青衿”。可见福州城内教育兴盛,教化入人之深。大历十年,这位“宗室才子”,终因劳瘁逝于任上,但他“为学而寓政”,取得显效,无怪乎福州市民闻其病故,无论“群吏庶民,耆儒诸生,雨泣庙门之外”,其政绩之感人可见一斑。而他的教化影响,更加广泛而深远:“由是海滨荣之,以不学为耻。州县之教达于乡党;乡党之教,达于众庶矣”。闽中文教之普及应由此始。
继任者有福建观察使常衮,于建中元年(780)贬而复起,以状元、宰相之身,入闽就任福建观察使,仍不忘职守,以兴学培士为急务。他同样推崇文教,礼遇士人,“为设乡校,使作为文章,亲加讲导”。对能诵书、作文辞者,即使是“乡县小民”,也“与之为宾主礼”,可见待士之诚。在他的教化下,“由是俗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文教成效大著。常衮同样卒于任上,后人尊之为“兴闽文学之圣人”。由是,福州儒学大兴,“学者益盛”。据《闽中记》载:“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是岁闽中四人登科”,令世人赞叹,“闽中自是号为文儒之乡”。福州因科举而声名鹊起,从此称“东南重镇”。
王审知主政闽中之后,继续其兄王潮之政,兴学重教,设四门学,倡设乡学、义学,普及教育。同时招纳延揽北方学士文人,其著名者有:韩偓、李洵、崔道融、王标、王拯、杨承休、杨赞图、王倜、夏侯淑、吴群、归传懿等人。他们或助吏治,或事教化,或治文献,闽中文教因此大兴。
在宗教文化方面,唐代福州佛教发展十分迅速。西晋太康三年(282),开始在州西北建绍因寺,到唐代寺庙显著增加,文宗时(827—840)增至39座,宣宗时(847—859),据郡人林谞撰《闽中记》载,已有存寺78所、废寺36所;懿宗时(860—874),有寺102座。诚所谓“殚穷土木”,以造宫寺,“极天下之侈矣”。而在唐末五代王氏治闽时期,“又增为寺二百六十七,费耗过之”。郭柏苍称:“王氏父子前后仅四十七年,计本州共增僧寺、尼庵一百零八所,此亦佞佛施僧之一证也”。只是福州城内的寺庵数目不得其详。据宋《三山志》载,有诗句云:“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由此亦可推知王闽时期寺庙之多。这从当时度僧数量中,亦可见一斑。《三山志》载,光化二年(899),王审知“奏度二千人”;唐天复二年(902),又在城内开元寺“度僧三千人”。其子王鏻变本加厉,于唐天成三年(928),在太平寺开戒坛,“度僧二万人”。王审知崇佛,下令张炉,备铜镴3万斤,铸造释迦弥勒巨型铜像。又以大量金银,制作金银字四《藏经》,各5048卷。
唐代福州对外文化交往,当以佛教高僧的入唐求法为主要。据记载,唐贞观年间(627—649),新罗(朝鲜半岛)僧人慧轮曾泛海来到闽越,后经此去往长安。唐天宝三年(744),鉴真和尚与日本僧人荣壑、普照等曾到福州买舟以东渡日本中国城市发展研究。唐贞元二十年(804)八月,日本空海和尚随遣唐使及留学生等入唐求法,遇风暴漂泊于福州长溪县赤岸(今属霞浦),后被营救,送往福州开元寺下榻,驻锡多日后于当年十一月北上长安。贞元二十一年,日本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第一舶,亦因遭遇风暴飘流到长溪县。唐文宗时(827—840),印度高僧般若怛罗在福州传授,慕名来学的日本僧人亦不少。唐大中七年(853),日本高僧圆珍(智证)和丰智、闲静等僧人附商舶自日本值嘉岛来福建,在连江登陆后,也进入福州开元寺驻锡五年,从师修习,向中天竺般若怛罗学习悉昙章、梵字和密教,向寺僧学《华严经》《俱舍论》等。可见开元寺已成日本、印度等外国僧人接待、修习之所。载籍有“新罗僧洪庆自唐闽府航载大藏经”的记录。可见新罗僧人也曾到开元寺修习,并收集运载佛经回国。因此,晚唐诗人的涉闽诗作,往往有这方面的吟咏之句。如马戴(卒于869年)《送李侍御福建从事》诗中国城市发展研究,有句曰:“宾府通兰棹,蛮僧接石梯”。表明福州接待宾客的府邸近海临江,乘坐海舶而来的海外僧人,下船登石阶即可方便下榻。据考此李侍御即为李远,于唐开成四年(839)赴福建观察使卢贞幕。同类的还有诗人李洞(约卒于897年)作《送沈光赴福幕》(一作《送福州从事》)诗,有句云:“潮浮廉使宴,珠照岛僧归”。记述的是福建观察使在江边饯别梯航而至的海外僧人归国的场面。这些都表明,福州地区的官员和文化人与海外宗教人士(主要应是佛僧)有着频繁而密切的交往。
中唐以后,由于陆上“丝绸之路”受阻,王朝重视发展东南与南方沿海各地的海外贸易,福州因此迅速崛起,再度成为海上“丝路”的枢纽。唐文宗于大和八年(834)还曾专门下诏,称:“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使、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说明晚唐时期,沿海各地对外贸易繁盛,税率收益大,朝廷十分关注,特别诏令地方长官慰问“蕃客”,善待蕃商,并让自由贸易。从该诏令中也可以看出,唐代福州港与广州、扬州并列为当时对外贸易的三大中心地区。其时福州对外通商贸易的地区不断扩大,除了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的传统航线外,还开辟了向三佛齐(苏门答腊)、印度与大食的航线,向东北亚的则有新罗(朝鲜半岛)与日本的航线,因而福州出现各国“梯航竞集”的壮观景象。唐末福州流寓诗人周朴有诗句称:“海水旋流倭国野,天文方戴福州城”。形象表明福州得天时地利之便,对外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遍及世界各地,异方殊域的客人闻风而至,辐辏星聚于福州城。福州作为对外交往的门户、海上贸易的枢纽,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瓷贸易的重要基地。

为确保最佳浏览效果,建议您使用以下浏览器版本:IE浏览器9.0版本及以上; Google Chrome浏览器 63版本及以上; 360浏览器9.1版本及以上,且IE内核9.0及以上。








 城市水资源排名资源型城市发展现状
城市水资源排名资源型城市发展现状 生活服务公众号公共服务图标
生活服务公众号公共服务图标





 中国各城市发展城市发展看哪些方面
中国各城市发展城市发展看哪些方面